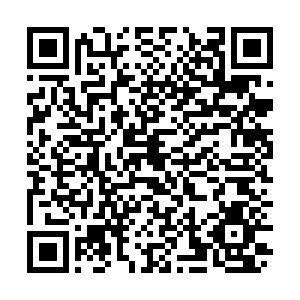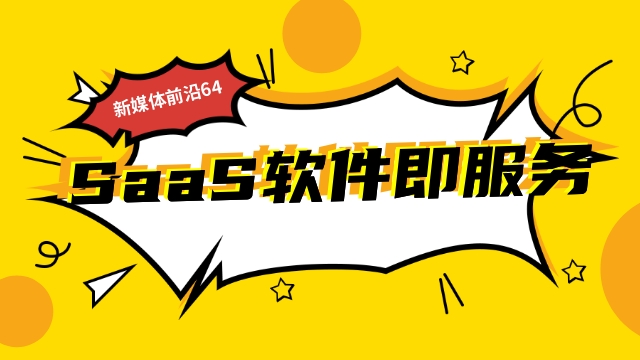

新媒体 | 2020-07-31 08:34
随着越来越多从事信息生产、传播、监控的劳动者以数字技术为生产和加工工具,且人类的知识本身不断以数字的形态存在,数字劳工日益成为传播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数字劳工”的研究与提出
“数字劳工(digital labour)”一词,从谷歌学术中输入关键词得出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传播学者是N. Dyer-Witheford在1999年发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说明了在电子游戏行业出现的高科技劳动力的男女分工以及地域分工问题。2000年,英国学者蒂兹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也提及到digital labour这一说法,她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劳动问题不能仅仅用资本家剥削这样的逻辑来分析……网奴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的一种劳工形式,他们更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关系”。她将这种劳动关系定义为“免费劳动(free labor)”。
对于“数字劳工”的研究,传播学界一直都在讨论,但是对于完整的定义,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直到福克斯在其《数字劳动与马克思》(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这本书中,对数字劳工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定义:“数字劳工是电子媒介生存,使用以及应用这样集体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一个确定的职业,他们服务的产业定义了他们,在这个产业中,他们受资本的剥削。”
“受众商品”的批判延伸
“数字劳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受众商品”的批判延伸。早在1951年, 达拉斯·斯迈思(Dallas.W.Smythe)就提出,商业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的注意力。1977年他发表了《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标志着其受众商品理论的形成。他指出,媒体广告时段的价值是传播产生的间接效果,而广播电视节目则是“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它们都不是广播电视媒介生产的真正商品。以广告费支持的电视媒介提供的“免费午餐”是喜剧、音乐、新闻、游戏和戏剧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受众来到生产现场——电视机前。斯迈思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时间都是劳动时间。并由此提出了在常人看来更加惊人的结论:“免费午餐”的享用者不仅仅是消磨时光,他们还在工作,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是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其不公平处在于,受众在闲暇时间付出了劳动,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其经济后果。
进入互联网时代,“受众商品”理论被西方学界进一步阐释与发展,“受众商品”的概念也与时俱进发展为“数字劳工”。英国学者蒂兹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在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的“高科技礼品经济”的理念上批判性地提出“免费劳工”(Free labor)的概念,她认为正是这些大量的免费劳工维持着互联网的运营。随着技术的发展,尤里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敏锐地观察到在游戏爱好者身上,生产和消费、工作和闲暇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进而提出了“玩工”(Playbour)的概念,指出“他们(‘玩工’)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网络游戏里,沉迷的同时,不知不觉免费为游戏商吸引了更多用户,创造了更多内容,改善了更多服务”。
“数字劳工”的逻辑争议:“参与”还是“剥削”?
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劳动的生产性实践在互联网时代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互联网改变了受众的角色,从原来单一的消费者变成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相统一的产销者(Producer)。数字时代关于劳动议题的研究放在媒体产业链的价值创造中去理解,试图解释网络平台的资本积累模式,用一种更为批判的视角来分析媒体产业的运营模式。这种剥削观的建立,使得所有的数字劳动问题最后的落脚点都在剥削以及如何进行剥削的问题上。
福克斯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受众与广告商之间的售卖关系仍然存在,他创造性地继承了达拉斯·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有一种新的商品形式,产销者商品(prosumer commodity)。产销者商品并不意味着媒体的民主化走向了参与式或者民主制度,而意味着人类活动的整体商品化。用户的每一次点击、浏览、转发、评论和授权等等任何线上行为都成为了对应网站或互联网企业的用户数据,并反过来精准地兜售我们想要的任何“商品”,进而从中牟利。但是用户这种价值创造的生产性行为并没有得到报酬。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传播政治经济学一大批学者研究得出的新的剥削形式,如监控、数据收集、内容创造等,这种隐藏在大众使用媒体所带来的快感是否是不是能成为一种对于这种剥削的一种补偿?
在经济层面上,这种补偿是无形的,但是在心理以及文化上,受众创造内容的同时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收集数据只是使用平台所带来的一种必要代价而已。
Mark Deuze以及John Banks就对网络时代的数字劳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受众对他们产生的价值不是没有察觉的。受众的这种免费劳动获取的价值更多的来源于一种认可,别人的评论、转发等都可以成为一种回报。并且随着受众网络版权意识的加强,受众对自己生产内容的价值的保护更加强烈,通过对版权的保护,受众有资格向平台以及内容扩散者要求回报。用户在互联网上分享信息,从经济层面上来看,这是一种经济行为,但是从社会文化上面来说,这却是一种维系社会关系,对于自身群体文化的建设,对于自己诉求的表达,这是“参与性文化”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上所获得的满足以及社会关系的建立要远比经济上被隐藏的剥削现象更重要。
就像特拉诺瓦所说:“他们(维持互联网运营的免费劳工)的劳动没有大量经济作为补偿,作为交换的是交流的快乐”。
参考文献:
1. 文森特·莫斯可,徐偲骕,张岩松.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J].全球传媒学刊,2018,5(04):127-139;
2. 汪金汉. “劳动”如何成为传播?——从“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工”的范式转变与理论逻辑[J]. 新闻界, 2018(10):58-66;
3. 赵小飞,名词 | 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2019(4)。
免责声明:本站所提供的图片部分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或网站,由本站编辑整理,仅供个人研究、交流学习使用,不涉及商业盈利目的。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本站管理员予以更改或删除,万分感谢。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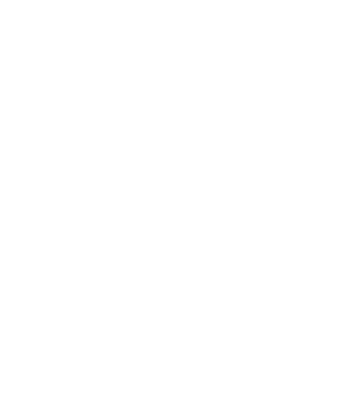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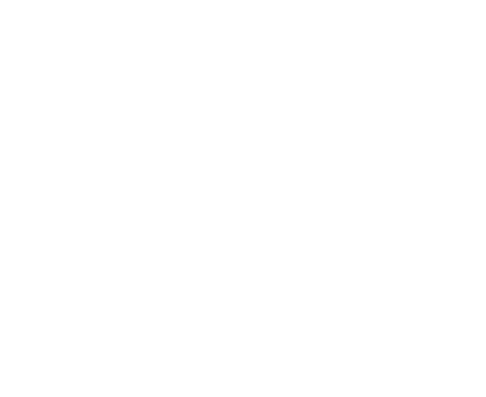 微信咨询
微信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