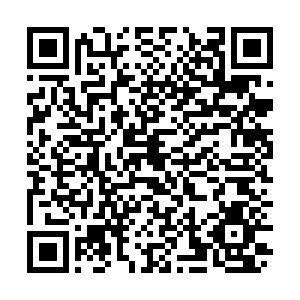论文跟读 | 2022-07-21 22:33
论文信息
●论文题目:A Review of Internet-Bas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发表期刊:Online Media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2022; 1(1): 124–163 Review Article
● 作者:Yong Hu and Lei Chen
https://doi.org/10.1515/omgc-2022-0009
Received October 1, 2021; accepted January 25, 2022;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16, 2022
另外指路胡泳老师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很多最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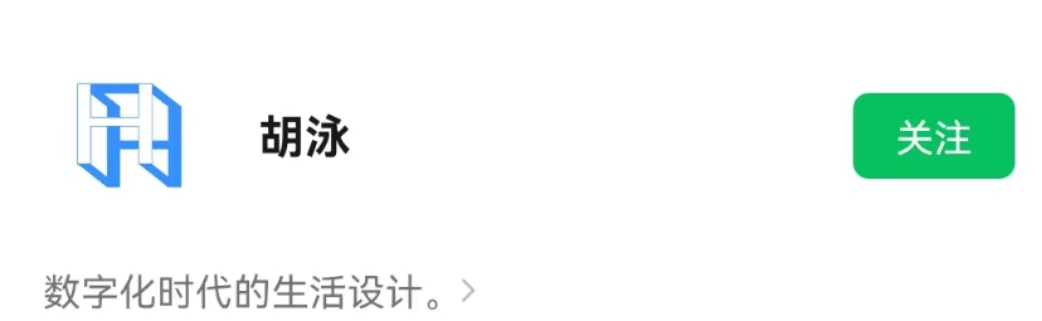
编者评述:
A Review of Internet-Bas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二十多年来,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了五个主要方向的分类框架。
首先是以媒体为导向的研究。这类研究试图总结网络媒介的内在属性,并推测网络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宏观影响。代表性的研究问题包括“新媒体新在哪儿”和“新媒介能给中国带来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吗?”这不是一种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但反映了传播学的人文研究传统。
二是面向用户的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通常是根据经验进行的。要么试着去理解不同的互联网用户以及用户为什么实际使用特定的在线媒体,或者分析互联网使用对用户的影响。代表性的研究问题包括“哪些因素影响老年人接受数字技术”(例如, Zhou 2018 )和“社交媒体是否帮助农民工积累社会资本?”(例如王和李 2015)等。这些通常是利用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使用经验性研究方法(例如问卷调查)或解释性研究方法。

(图源 https://callhippo.com/)
三是现象导向的研究。这类研究试图了解用户在使用网络媒体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现象,这些现象有什么特点和规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包括互联网事件、网络文化等。代表性问题包括“促使网络事件爆发的影响因素有哪些”(Li 等人,2013 ),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多样化。
四是政策和对策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并不热衷于探索基于互联网的传播现状,而主要旨在帮助政府部门、公司和组织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问题包括“互联网时代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例如张和施 2020)。
五是批判性互联网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不是为政府部门、公司等建制服务,而是批判性地分析现有制度是否自由公平,揭示制度对公众的剥削。代表性研究问题包括“网络小说平台如何动员作家进行高强度劳动”(如胡和任 2018 )。
本文分别从这五个方向来梳理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的成果。
新媒体“新”在哪里
中国学者用“连接”这个关键词(Gao 2010 ;Peng 2013 ;Yu 2016),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现了新媒体的演进逻辑:
首先是机器对机器的连接。前 Web 时代在解决计算机到计算机连接问题上有了重要突破,使全球互联网成为可能。其关键技术是分布式网络和 TCP / IP 协议。
第二是内容连接。这一阶段的互联网也被称为 Web 1.0,其重要突破点在于解决了内容的聚合和呈现问题,使互联网上的所有信息相互连接,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内容网络,即万维网。其关键技术是超链接。
第三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这个阶段,互联网也被称为 Web 2.0,在激活个人和他们的关系网络方面有了重要的突破。个体可以绕过门户网站所代表的信息中介,建立自己的沟通中心,通过各种关系链与外界互动,传播和接收信息。互联网就这样进入了个人的时代。
最后,还有万物智能互联。它可以被称为 Web 3.0,以物质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的全方位智能交互为特征。在未来,任何存在于各种环境中的对象都可能成为智能代理,可以自主地发送或接收信息,实现事物之间的智能连接和交互,而不是完全受制于人。
新媒体对中国的影响
在分析新媒体传播特征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这些特征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从而构建了一个“沟通工具的改变—沟通模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沟通关系的改变—价值观的重构”的逻辑。
在宏观层面上,影响最大的是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Yu等人(2016)指出,过去 20 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交往的场景和方式,推动社会关系网络从一个“差异化的联想模式”和“组织化的关联模式”向开放、互动、复杂的分布式网络转变,引发了资源分配规则和权力分配模式的变革。
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来源,互联网激活了个人和自组织团体,赋予了社会中“相对弱势者”权力,并将权力和垄断资源从国家转移到非国家行为体。
新媒体的出现也重塑了很多竞技场的价值逻辑。几位学者注意到,新闻业的基本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彭兰(2012)指出,受众现在可以以公民新闻为参照,判断专业媒体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客观性和全面性。社交媒体议程正在影响专业媒体议程。蔡和玲(2020)认为,经过新闻领域多个行为体的介入,新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果:新闻成为多个主体之间合作和竞争的产物;新闻更多地是基于观点而不是基于事实;传统的新闻矩阵被社交媒体的新叙事所推翻。

(图源 https://www.linkedin.com/)
易(2017)认为,新闻价值观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新鲜”到“活”,从显著性到有用性,从地理接近到心理亲密,从人情味到取悦大众。陈(2019)认为,新闻内容本身的魅力已经被新闻修辞的魅力所取代。
在新闻实践方面,王等人(2014)观察到了“新闻内爆”,指出当前的专业新闻已经过度依赖“内部生产”(很大一部分新闻报道不再关注外部世界,而是聚合和合并现有的新闻故事),“衍生产品”(绕过难以获得的核心事实,而倾向于容易获得的外围事实),“重定向生产”(相当一部分内容不是记者自己生产的,而是从其他媒体重定向的)。这些报道方法没有有效地回应受众对确定性的需求,反而通过巨大的信息泡沫进一步迷惑了人们。Yang 等人(2018)分析了“新闻漂移”现象,如夸大的标题和评论,假新闻泛滥,甚至新闻概念越来越偏。
新媒体改变日常生活
媒介技术的运用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类。
一类关注内容生产者的传播实践,尤其是网络时代专业新闻生产者和媒体机构。比如, Wang(2010)发现,在新技术带来的剧烈环境变化的冲击下,构成传统新闻实践结构的三个最重要的要素——配置资源、生产规则和权威资源——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无论是在获取信息源、建立新闻生产规则、还是期待社会认可方面,传统新闻实践的结构性特征在当前数字化新闻生产中仍然发挥着稳定和制约作用。这样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看清传统媒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变”与“不变”。
另一类关注的是用户,尤其是农民工、青少年和大学生( Huang 2015 ;Liu 2017 ;Wang 2014 ),妇女(曹, 2009 年;李和杨, 2015 年;孙和侯, 2016 )、少数民族(孙, 2016)和其他群体在二十一世纪使用新媒体,以及新媒体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通过揭示影响媒体技术采用的相关因素,研究人员触及社会资本,媒体使用者的身份、知识差距、政治参与和幸福感等多种方式,观察和理解人们如何在互联网上进行社会互动和意义建构。例如,大量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是利用新媒体的活跃群体(宋 2016 ;周和吕 2011),但主要是为了交流和娱乐,而不是为了积极关注与自己兴趣相关的公共信息,积极构建专业人脉(何和严 2016 ;王 2013 ;周和吕2011)。
这种研究有助于打破不同社会阶层的成见和误解。它不仅加深了对媒体技术潜力的认识,也为后续思考如何改善未来传播提供了借鉴。
新媒体对个人的影响
在微观层面,即新媒体对个体的影响,其影响更为多元,涉及个体认知、理性程度、自我意识、情感等多个维度。
例如,在自我意识方面, Chen and Hu(2020)发现抖音为用户提供了一个高选择性的自我参照系统,并推广了一种独特的价值标准,而观众则通过漫无目的的沉浸式观看、共同观看者的想象和特定的交互方式实现认知自我,完成对社会阶层的价值感知。
另一个例子,为网络对话提供了新的启示,Jiang and Hua(2014)认为,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和个性化使得亚文化的传播更像是独白。人们越来越自我对话,沉浸在自己创造的网络迷你世界中。
在众多研究中,有一类是比较特殊的——中国人对国外网络媒体的使用。这类研究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散居群体使用外国媒体的效果(当事人仍在本国境内);另一种是散居群体使用外国媒体的影响(当事方不在本国境内)。对于前者,研究的重点是新媒体对政党的国家认同、政府信任和个人认同的影响。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传统官方媒体的使用频率和信任度显著增强了中国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而外国媒体使用频率及信任度则显著削弱了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Zhu and Ren 2020)。
网络空间的集体行动
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空间中各种类型的社会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话语表达)的特征。无论是公众舆论还是具体事件都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
关于网络舆论,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探索传统传播“规律”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举个例子,刘(2001)examined,“害怕孤立”和“开放表达”的因素源于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基本假设,并将其放到一个网络环境中,得出沉默的螺旋的基本条件在网络空间仍然存在的结论。同时,他通过对“脊梁”的分析,揭示了数字媒体中沉默螺旋的一些独特效果。

(图源 https://twitter.com/)
2003 年以后,网络舆论的力量在中国社会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如果说以前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不具备传统媒体那样的“造势”能力(梁 2002),那么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中国网民通过网络舆论展示了他们改变事件进程的力量。因此, 2003 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年”。
此后,经过几年的发展, 2008 年,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老虎照片盖奇”到汶川大地震,从瓮安群体性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一系列涉及面广、性质各异的事件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网络舆论对政治行为的塑造和制约作用。2008 年 6 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并通过强国论坛与网友交流,体现了中央领导层对网络舆论的重视。相关研究也反映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研究人员开始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舆论渠道(王和丁 2004 年)。而且,这一渠道在舆论监督和警惕网上反腐力度上一直卓有成效。Du and Ren(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从 2004 年到 2010 年,网络反腐调查的数量逐年增加;网络曝光缩短了腐败调查的时间,使腐败惩罚更加及时。
随着网络舆论的兴起,学术研究思路也从检验旧理论演变为试图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主要涉及具体现象的概念界定、现状描述、类型分类、表征、总结、机制追溯、后果评价。
在概念界定上,一些研究认为,尽管“网络群体性事件”一词在我国被广泛使用,但它实际上是“网络”和“群体性事故”的结合体。它延续了官方将社会动荡归为“群体性事件”的立场,并将导致网络舆论聚集的污名化。更科学、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互联网公共事件”。但是,任何导致严重冲突的互联网公开事件,都反映出对话沟通的缺失。网络公共事件的展开过程既是一个舆论过程,也是一个符号建构过程(李董 2012)。

(图源 https://www.cequens.com/)
一项实证研究发现,从 1998 年到2009 年的 160 起重大事件中,大多数起了积极作用,其积极意义非常明显(Zhong和Yu, 2010)。有研究指出,互联网初步形成了政府与网民良性互动的格局,但随后的严格监管,导致网络意见领袖活动下降,公众表达热情消退(李郑2014)。其他研究指出了一种“舆论泡沫”现象,即过多的网络言论可能会导致一个事件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时被另一事件所取代。存在着试图通过事件替代形成舆论和舆论转移的严重问题(Zhang 2014)。
为了追溯群体性事件的机制,Yang(2009)认为,网络事件的发生并不取决于资源调动或政治机会。关键因素是事件本身令人震惊的性质和描述方式:给人以道德震撼的帖子可以刺激网民的情绪,调动他们的力量,从而酝酿网络互动,引发网络事件。
然而,其他学者正在探索可能影响互联网事件的多种因素。一个大型数据集的分析发现,发生地(地点)和公众吸引力(目标)是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必要属性,与之前的设想不同,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那么重要(Li et al . 2013)。一项研究发现,接触传统媒体的强度和对新媒体的信任与农村人的环境抗议有关(Lu et al . 2017)。
在后果评价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早期,也许是因为很多研究者来自公安系统,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群体性事件的安全影响和社会控制上。这些研究者倾向于从社会动荡的视角来看待网络事件,他们的价值判断也被模仿。完全忽略了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语境差异,以及网络群体性事件动员模式的变化,从而持有明显的负面评价(董和王 2011)。
随着传播学等其他学科学者的进入,相关研究的视角开始多元化,立场不再趋于极端。不少学者肯定网络行动的积极意义,如缓解社会压力、为弱势群体提供话语空间等;然而,他们还强调,必须警惕其负面影响,如引发恶毒的舆论和造成治理危机。
网络中的文化参与
互联网不仅带来新的信息交流手段,也为文化创作提供了新的空间。研究者早就认识到,互联网已经形成了比大众传播时代更为复杂、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关于网络文化的本质,许多研究者认为它是草根群体以仪式的方式反抗主流文化、表达自己独特价值观、形成身份群体的一种方式。
在众多的特征中,“参与”被认为是许多亚文化的共同特征。蔡和黄(2011)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带来了一种新的参与文化。网络不再像传统媒体那样以内容为中心,而是形成以用户生成内容和人际关系为中心的虚拟社区,从而为过去隐藏在利基中的亚文化提供了新的舞台。
当然,不同的互联网文化也有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与传播这种文化的媒介本身的特点有关。例如,Jiang and Hua(2014)认为潮人亚文化(小清心)呈现了风格的巨大变化,催生了一种温和对抗的艺术。Yang(2017)指出,快手把互联网带回了一种最原始的草根文化,给予每一个普通个体平等的待遇和话语权。

(图源 https://pixabay.com/
images/search/communication/)
然而,尽管互联网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反抗精神,但普遍认为其反抗效果有限,容易被商业力量收编,推动消费主义。例如,潮人亚文化的风格和品味被商家借用,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时尚(江和华 2014)。邵认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转型,反抗显然不再是当今亚文化的核心特征。如果说反抗真的存在的话,那也只是以一种不直接对抗主流的方式存在,而是“小心翼翼地反抗,小心翼翼地屈服”,“和自己玩”(邵 2018)。
也有人认为,表面上的抵抗实际上可能会加强既定的权力,如商业力量的统治。Lv 和 Xu(2016)在对重叠评论(单目)的分析中认为,单目保证了观众对视频的持续使用和消费。在这个过程中,丹牧的使用者只获得虚拟的快感,却没有果断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体验和享受的所谓“自由”,来源于比传统媒体消费更多的时间和投入更多的精力。
即使没有被商业化拆解,这种反抗也可以在解构权威的同时轻松解构自身。Zhang(2016)认为,以百度贴吧上的青年爱国运动为代表的网络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抵抗”,最终导致了“假想的解决方案”。
管它有很多局限性,但也有学者看到了网络文化光明的一面。根据Chang(2015)的观点,即使一些互联网文化创作者最终选择向主流文化妥协,或者进入传统内容生产领域,互联网世界发展起来的关于文化生产的价值观、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必然冲击主流文化生产机制,从而改变国家和市场主导的主流文化的某些方面,并迫使它们进行自己的创新或吸收更多元的文化视角,从而为扩大文化民主乃至政治民主做出贡献。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政策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主动与最好的媒体和面向用户以及现象驱动的研究发现对接,而且能够将这些发现转化为真正相关的政策和应对措施。
例如,在如何改造传统媒体方面,Peng(2018)提出了三条路径: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对于移动转型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受众通过移动设备访问更多的视频等内容,但同时也表明用户在内容消费上的偏好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追求比过去更活的感觉,在几秒钟内做出消费决定。因此,移动化不仅意味着传统媒体需要将移动视频等移动内容作为新的生产方向并将其常规化,同时,它还需要适应移动时代的用户喜好,比如摒弃传统叙事公式,力求在短时间内形成视觉亮点。在走向社交、走向智能方面, L . Peng 还提出了“用户分布”“用户生产力”等理念。
一个好的政策研究必须产生新的观点,或者揭示以前被公众忽视的某些点,或者澄清常见的误解。例如,Wang(2021)提出了在中国对外传播的不同活动中“重新分配资源”的想法。他认为,中国对外传播没有达到应有效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太多的资源被投入到美国垄断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诚然,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汇聚了大量欧美用户,但如果他们对中国的态度能够得到转变,将极大地帮助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然而,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量巨大的情况下,很难吸引西方用户的注意,增加他们对中国的好感。虽然西方的超级政治营销并不能保证在互联网上取得有说服力的结果,但中国自己的官方信息传播更没有希望。与其将资源浪费在这些传统渠道上, W . Wang 认为,这些资源中的一部分应该用来动员国内青年积极参与中国的出境基层活动,让他们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使者。
互联网在给人们带来选择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烦恼。从数字资本主义到数字劳动,从数字鸿沟到隐私问题,这些主题也成为相当多研究的焦点。
对于数字资本主义,Li(2021)指出平台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让数字平等主义幻灭。传统上属于非生产性材料的个人数据和关系被私有化。对于媒体制作,所有专业和非专业的社会劳动都被纳入平台劳动体系。媒介数字劳动的主客体身份被整合,新闻、娱乐、休闲活动交织成资本主义生产链。整个社会都在为平台公司从事剩余价值生产。
对于数字化劳动,许多中国学者通过定性研究,研究了数字劳动平台如何影响工作条件,如Qiu 的研究(2017)在 ICT 制造业的数字劳工,Dong et艾尔Song(2021)对直播节目中女性的研究,以及 Song 对动物穿越游戏玩家的研究。J.Song 发现,《动物穿越》游戏预先设定的叙事任务将玩家从休闲转化为劳动;低难度、盲盒、评分和活动策略让玩家克服重复的无聊;玩家的内容创造和分享让他们成为主动的劳动者。两种网络系统进一步加剧了劳动:主机网络的社会性强化了商品拜物教,互联网催生了不同类型的玩家群体,从而形成了围绕游戏的玩家产业链。

(图片来源https://www.linkedin.com/)
关于数字鸿沟,Hu(2020)指出,传统的知识鸿沟仅仅是知识或信息的差异传播,而今天的数字鸿沟是关于使用的质量而不是获取的质量。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上,许多服务默认设置为“数字”,而非互联网用户面临边缘化的危险,这威胁到某些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权利,从而造成“数字放弃”的问题。促进边缘化群体使用信通技术的目标不是克服数字鸿沟,而是促进社会包容。
对于隐私问题,Sun and Tang(2017)提出,要打破移动时代的“隐私悖论”困境,需要多层次的在线隐私约束和控制,其中包括:建立有关数字隐私的规范;平衡个人控制其个人数据的权利;加快建立适用和合理的隐私期望;提高用户的数字素养。
同时,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造成了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之间的不平衡,因此胡(2020)提出了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三个原则:
第一,将公共利益视为隐私的例外;
第二,如果真的有必要为了公众利益而限制隐私,则必须在限制过程中为基本公民权利和个人利益确立适当的保护;
第三,维护在危机中收集的信息的公平使用。这些原则的出发点是,隐私本身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利益。
正如 Hu(2020 ,第 5 页)所总结的,“数字社会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复杂而棘手的,比如个人隐私与社会开放的冲突、安全和自由、商业和社区、政府监督和个人自主、蓬勃发展的创造力和保护知识产权、日益包罗万象的互联网平台以及迫切需要维护用户权利,仅举几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革命远未结束,或者说“被数字化”的问题比“成为数字化的”问题严重得多。”
这是一篇综述型的文章,很适合同学们用来了解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概况,大家有兴趣还可以深入阅读文章里提及的一些具体研究。
文章内容丰富详实,涵盖了数字劳动、平台经济、数字资本主义、数字鸿沟、对外传播等高频、前沿考点,尤其对于新媒体领域研究的总结梳理非常透彻,希望大家认真阅读。
更多内容欢迎咨询助教老师,微信扫一扫即可添加哦~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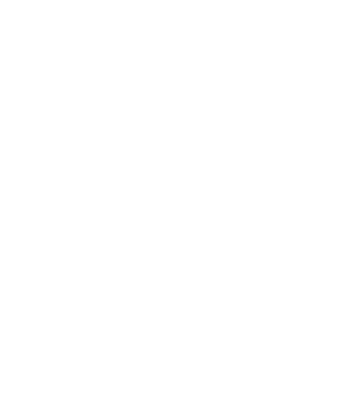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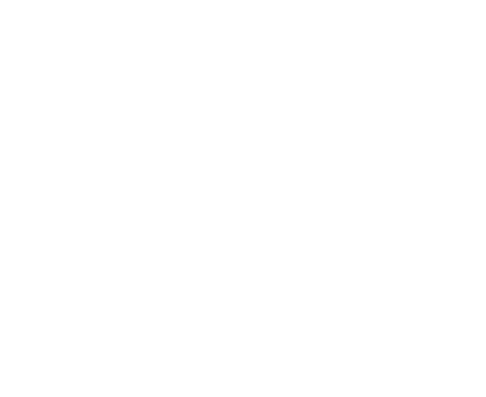 微信咨询
微信咨询